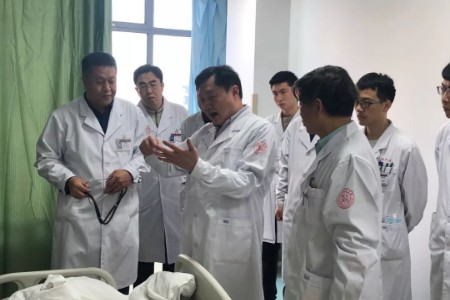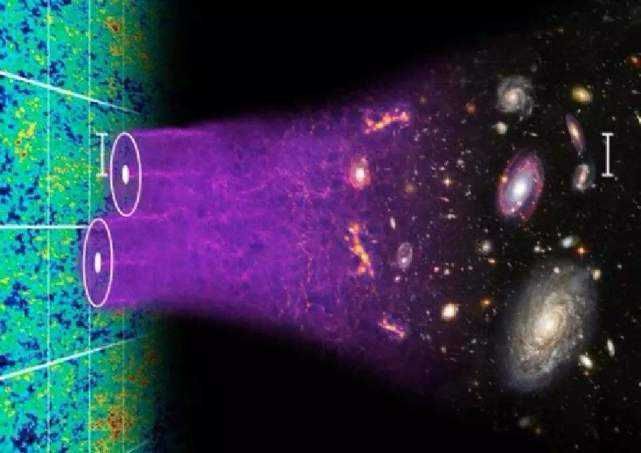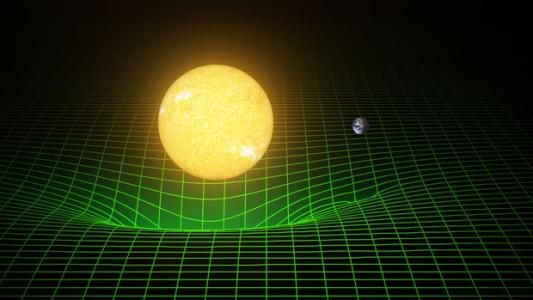早年,耿军力初到北大人民医院,目睹一例恶劣的医患纠纷。一位患者做完鼻子手术,老觉得不舒服,就认为手术没做好,狂躁失控,持刀行凶,两位医生受伤,或脸部遇刺,或腰部被捅。从医多年,大的医疗事故间歇发生,小的隔三差五的不断。医患关系在当下,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相互沟通有问题”。医学上有许多专业的东西,患者不知。医生认为正常的,手术做了就要出血嘛,患者看见血惊恐,觉得出了岔子。信息量不同,认知就不同。医学的门槛高,不可能要求患者熟知这门学科,这里面就有一个信任问题。我信任你,你的所说所为,即是合理;我不信任你,患者疑心,医生小心,一件小事就可以闹起来。
耳鼻喉的手术风险大,耳、鼻、喉全在脑袋上,手术一旦触到面神经,面瘫了。手术风险大,限制了耳鼻喉在多数医院的发展。
人通七窍,窍与精气神关联。很多患者先有心理问题,淤积到耳鼻喉。或有中年女士,来医院求救,说是嗓子有东西,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恐是得了癌症。检查无异,女士大呼:怎么可能没有?我觉得明明有嘛。
这类患者疑心大,或有幻听,或有幻觉,这是臆病,不是纯粹的耳鼻喉病症。反观医患的暴力事件,有的冲突不在医学上的尺长寸短,而是心理疾病患者的爆发。
医生这个职业,颇受尊重,待遇稳定,一朝离开舒适区,恐慌难免。离开体制意味着什么,出来混要靠自己,变数不定,随时都会有变化。你在体制内待的时间越长,越难离开。去留之间,难的还是你自己的心理障碍。“我还算有勇气去面对变化,好在呢,我在体制内待的时间不是那么的长;而且呢,我刚离开那阵,有的同行就说我离开体制晚了”。停在体制的时间短,割舍的时候就不太痛。“我的同学有早出来的,那个时候,国外医药企业进驻中国,专业人才奇缺”。早出来,机会就多,占得先机。
1999年,耿军力入职美笛乐听力植入技术服务公司,任市场总监,在国内推广奥地利人工耳蜗。这些外企医药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产品本身就是专业领域,还要涉及到手术流程,“你要和手术的医生搭得上话,没有医学背景的话,你很难和这些大医院的医生交流。我在公司做技术的推广,第一要和医生沟通这是怎么回事,指导手术”。
植入人工耳蜗是目前失聪儿童恢复听力唯一的办法。人工耳蜗的原理类似麦克风,失聪的人群,声音抵达耳朵,无法转化为神经的信号,就像麦克风坏了,接受到声音,不能转化无线信号扩散出去,喇叭放不出声音的核心是“转换功能出了问题”。人工耳蜗可把声波的振动转换成神经的信号,传递给大脑。
婴儿出生后,走例行的新生儿筛查,在这个环节,一些父母震惊地发现孩子听力有障,瞬间天塌了,忧心如焚,或寻中药,或诊针灸,或服各种各样的西药丸,“几乎所有的失聪家庭,这个过程都要走一遍”,最后才相信,单纯地吃药无济于事。这个过程很难,不单是花了多少钱,孩子受了多大的罪,家长跟着几许折腾,还耽误了植入人工耳蜗的最佳时机。为什么说十聋九哑?听力与大脑的发育紧密关联,孩子出生后,如果一直没有声音的刺激,大脑中枢的语言区域就不能发育。没有声音,何谈言语?
耿军力接触到许多失聪孩子的家庭,印象深刻的有两个家庭:一则贫,一则富。贫者是农村家庭,领养的孩子,最初看不出孩子有听力障碍,慢慢发现孩子老是不说话,到医院一查,耳朵有问题。这对来自河北的父母没有放弃,百般寻医,找到了耿军力的公司,申请为孩子植入人工耳蜗。钱凑来凑去还是凑不够,父母救女心切,道出领养的隐情,耿军力听了悯然,“行了,就这些钱吧,做吧手术”。这个孩子的妈妈很坚韧,在北京做保姆挣钱,送女到康复中心锻炼耳力。而今,这个小女孩已上初中,“聪明活泼,听力与常人无异,看不出一点问题”。她的妈妈懂得感恩,“一直记着你,逢年过节的发个短信”,这个妈妈一抛过去的愁眉苦脸,开心打工与女留京生活。
有对富人夫妇,“有钱,但不信”。整天找你聊,你给他说完吧,他要去验证,各方面去打听,夫妇俩人,每次拿着本记录,今天问什么了,耿军力怎么回的。然后各大医院打听,折回来再回来,一条条证实,“你上次说的,别人说的和你不一样,怎么解释”。如此,来来回回五个月,终于下定决心了,手术前,纠结的不得了,要求手术万无一失。耿军力如实说,只要是手术,无法保证百分百的成功。
术后,这对夫妇的期望值很高,单请老师教女儿恢复听力,事无巨细,不分时间,问话耿军力,“我有时候实在是烦了,但是忍一忍,需要理解他”。女儿康复了,正常入了小学。女孩留发,耳蜗形似发卡,别在发际,或隐于发内,老师同学不知。
富者设宴请耿军力,孩子爸爸说:“唉,这么多年没少麻烦你,说句实话,我有这样的孩子,我有心理毛病。原来我有许多时候做的过分了,现在孩子康复了,我也长吐一口气。”
在医疗圈多年,耿军力感叹:中国人对医学了解的太少了,对生命对身体又关照的不够,大家似乎有种心态,“我负责折腾,医生负责治病”。未来的中国,生命科学与健康管理是刚需,也是大势。为此,长江商学院启动“生命EMBA课程”,开风气之先。
比较其他发达国家,医疗环境较好,“多数患者很信任医生,这是一贯的从业氛围”,另外,国外的医疗保险体系完善,保险覆盖人的生老病死。婴儿一旦通不过听力筛查,待到半岁确诊,建议植入人工耳蜗,外有保险,内有信任,“这个手术过程就会很顺”,在国内,如在半岁确诊失聪,医生建议家长做手术,多数家长不听这个,心存疑云:做这个手术,医生有什么好处,可能有提成。说不定,吃点药就治好了。这些家庭非得绕个大圈子才回来接受现实,核心就是医患之间缺乏信任。
国内的医患关系紧张,医和患都有问题,甚或有恶性循环之态。在诊断过程中,医生执行一种尽量撇清己之责任的治疗方式。有患者来,脑袋上磕了一个包。医生见了,担心有变,咔咔咔,令患者去做CT;咔咔咔,令患者去做核磁。患者晕了,不就是一个包吗,不就是划一个口吗,何苦这样折腾?医生真有顾忌,不照仪器,颅内出血咋办?单纯外伤治疗,患者就会诉其误诊。实际上,这种几率极少,但医生为了防范万一,主推耗时耗财的诊疗手段。
医生有真委屈,觉得病人不懂感恩,依赖仪器,忐忑从医,给予病人详尽解释,不见得好,也许病人会反咬一口。这就像开车,开车总有个追尾撞车的风险几率,你万一撞车了,不能一味埋怨汽车公司吧。患者这边,到了医院,揣着小心,只要医生开药,就算今天医生该挣多少外块。我这一个小病,开了几千块钱的药,还了的。这样下去,医生越保守,患者就有更多的抱怨。
医疗本身就是一门不断试错的科学,当医生不愿冒险,不敢冒险,那么这门科学的步子就慢了。在生命科学健康管理的领域,信任比技术重要,这里有医患之间的信任,有医生与医院的信任,有政府与医疗队伍的信任。彼此信任,才是寻医问诊的第一个挂号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