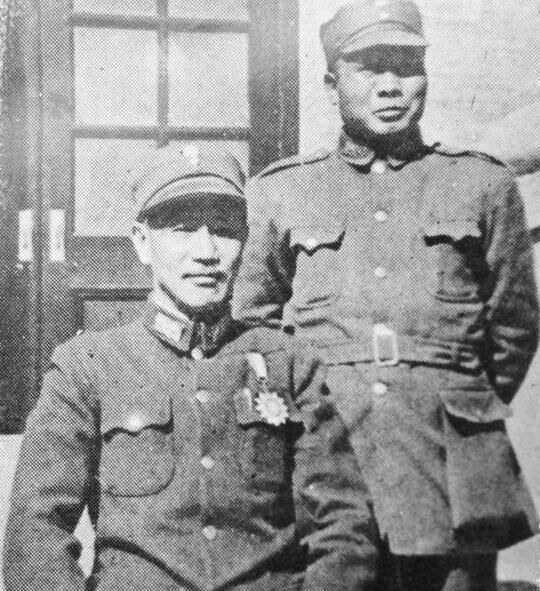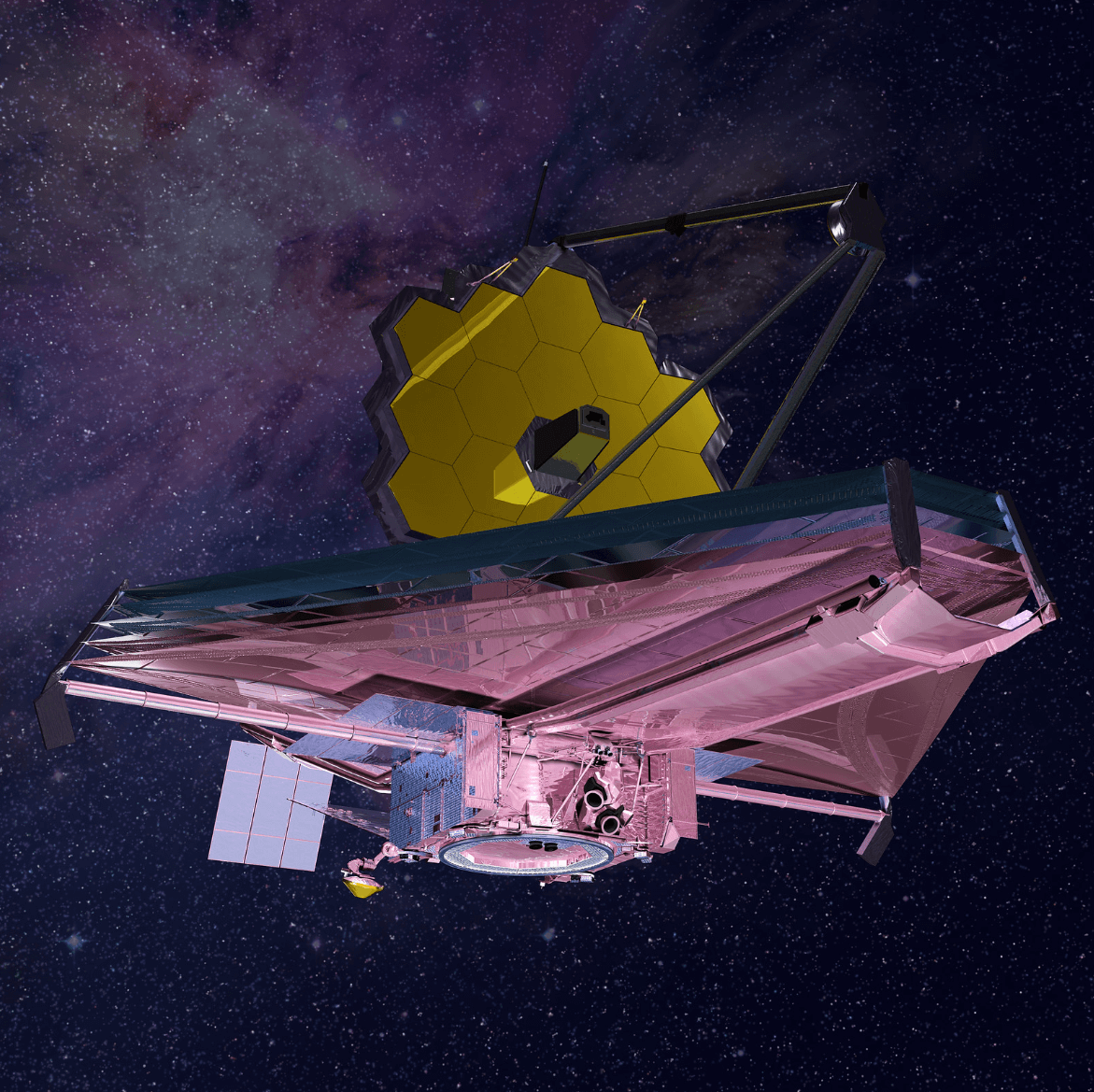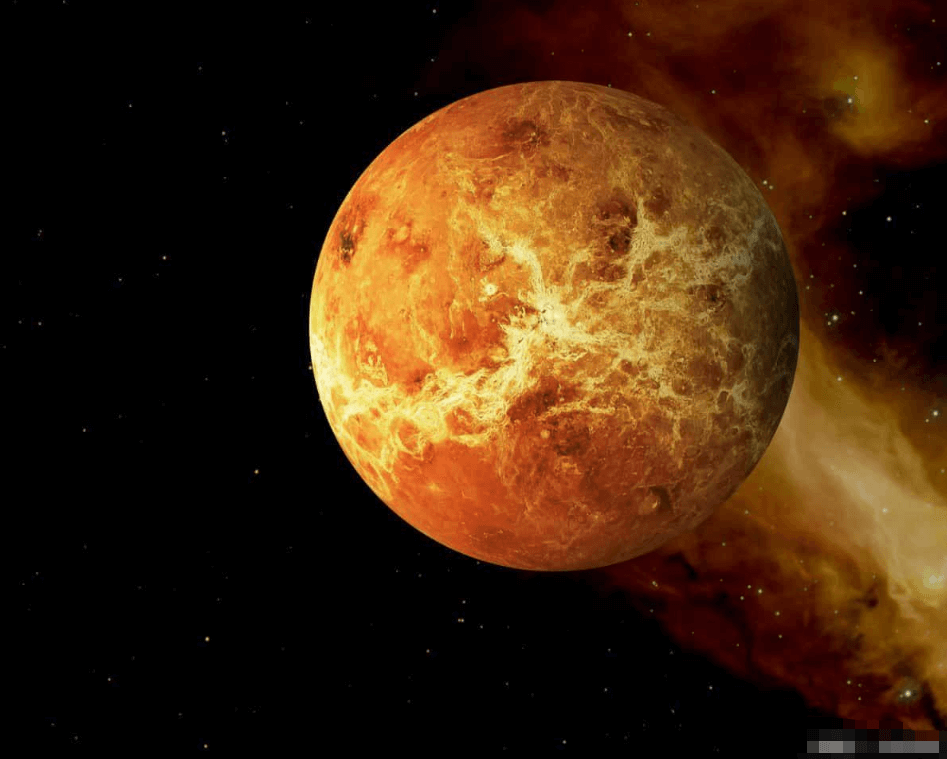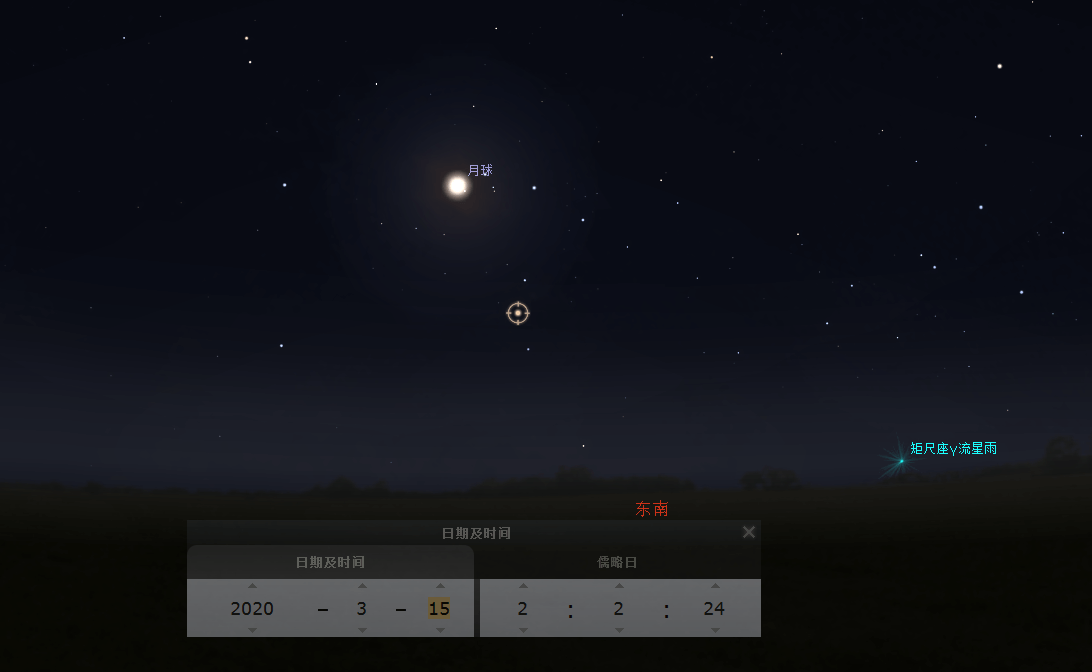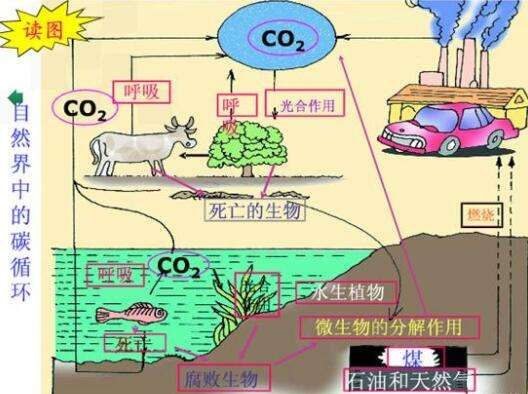1966年对《纽约客》来说是个好年景,它卖出了6100页广告,发行近45万份杂志,继续占据美国杂志排行榜第一位,也是史上发行量最多的一年。但到了1967年,《纽约客》却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失去了40%的广告,杂志纯收益也从三百万美元骤降到一百万美元。
危机发端于一篇报道。1967年7月15日,《纽约客》刊登了一篇名为《边水村庄》(TheVillageofBenSuc)的报道,作者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乔纳森·谢尔(JonathanSchell)。这篇文章是谢尔的一篇战地报道,他在毕业后前往越南旅行,在西贡受到了美国军方的礼遇,被允许成为采访战争的战地特派员。在当时美国国内主流舆论中,越战是为了抵御共产主义侵略力量,拯救越南于水火之中的正义战争,但谢尔看到的却是一场残忍的屠杀和轰炸,以及随战争而解体的越南社会结构。
带着震惊与困扰的谢尔回国后向一位朋友谈起了此番见闻。他的这位朋友就是《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Shawn)。肖恩对越战一直心存怀疑,他鼓励谢尔将见闻写成报道。于是,谢尔完成了一篇描述越南乡村与美国士兵遭受攻击的报道,从这篇报道开始,《纽约客》刊发了一系列批判越战的文章。
一份弥漫中产阶级雅趣生活价值观的刊物突然向国家开火,《纽约客》很快成为了迷醉在60年代“新左派”运动中的美国大学生的新发现,但保守的中年读者对《纽约客》的批评报道明显表现出了反感,不少年纪较大的用户停订了杂志,而他们不仅是《纽约客》的主要读者群(1966年《纽约客》读者平均年龄为48.7岁),也是杂志广告页上昂贵的钻石腕表与胸针的主要客户。
流失掉中高端读者,也意味着杂志被广告商逐渐疏远。《纽约客》的股东们召开了一次集会,会后股东们告诉肖恩,不要再继续吸引“错误”的读者,要马上改变对越战报道的编辑政策,否则就走人。
肖恩并未认错,反而回击老板:“我不愿意将‘读者’说成是‘市场’。我不要让他们觉得对我们只不过是消费者,我觉得那是令人厌恶的。”为自己的这段陈述,他搬出了《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和《读者文摘》的例子。“这些杂志在开始并未顾及到市场,而是表现出其个性价值,从而能够成就‘帝国’,并且建立长程认同。”
之后的故事是,《纽约客》并未改变越战报道的编辑方针,在1969年,记者西莫·赫许(Seymouthersh)在《纽约客》刊发了美莱村屠杀的报道,这篇关于美国陆军屠杀越南平民的报道,震惊国家,也令赫许获得了1970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纽约客》通过长时段的恢复,在1980年经营回到了纯利润三百万美元的位置。而其读者年龄则在数年间急剧下降,按照1974年的统计,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仅从纸面上看这个状况,很容易被小报编辑安上“失去的十年”之类的标题,但不要忘了,在二战之后一直到80年代,美国报刊界陷入在整体萎缩的状况中,电视屏幕分走了广告商的预算,国内剧烈变化的意识形态,也叫读者分心,与1929-1942年的萧条时期相比,美国人的个人收入提高了四倍,但报刊却遇到了史上最坏的读者流失状况,1980年一年中,美国有17家报纸停刊。如果把《纽约客》的复兴安放到这样的背景下,这本杂志的经营堪称健康。今天,《纽约客》在互联网的时代,同样面临广告量下降的局面,但作为整体品牌,它也在杂志订阅、品牌产品和活动中找到了一条留住读者的盈利之路。
价值观到底归谁所有?
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媒体公司化程度越来越高,许多媒体在组织架构上已经与大型商业机构无异,但像《纽约客》这样的媒体,编辑部却几乎是去公司化的存在。肖恩在60年代所说的“长程认同”已成为编辑部与市场部门分离的一条重要意见。媒体与普通商业机构不同的一点是,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是影响民主政治的重要单位,价值观不仅是空泛文艺的新闻理想,而且是切近利益的品牌标识。
建立长程认同的价值观,在广告成为报刊商业基础后,即成为了现代报刊的经营基础。在19世纪,诺斯克里夫勋爵(AlfredCharlesWilliamHarmsworth)将报纸从印刷厂手中夺走,交到广告商手中前后,因为工新经济阶级的崛起以及印刷术的发展,英国报纸开始了分化之路。《泰晤士报》从参与“乔治四世废除卡罗琳王后头衔”的论战,到对改革情愫的发阐,获得了敌视王权的中产阶级源源不断的广告支持。《每日邮报》则走上了平民路线,它对于南非战事的报道为它吸引了众多中下层、拥有帝国情愫的工商业者以及公务员。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时期,它的发行量达到了100万份。,而三年前的创刊号,只销售了不到40万份。
透过共同价值观的分享,媒体与受众可以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媒体向受众售卖精心挑选并择干洗净的观念,受众则为共鸣而付费。
如果像《堪萨斯明星报》发行人尼尔逊(W.R.Nelson)所言:“报纸是在餐桌上供人阅读的。”那么在什么样的餐桌上供人阅读,可视作不同报刊价值观的区别。桌上用铁盘盛着法式龙虾,或者是一碗街头的兰州拉面,也许对一个好胃口的人来说没什么区别。但对于广告商来说,龙虾还是拉面,意味着这个坐在桌前、正在翻看报刊广告的人是否买得起一辆新出厂的奔驰跑车。因此,许多希望吸引奢侈品广告的杂志,在经营策略上放弃了下层读者,充斥着黄页信息的小报则热衷于传播廉价八卦和翻译信息。
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知音》可以上市,《参考消息》长盛不衰。但一些城市杂志将自己的读者群定位在屌丝阶层,就令人觉得像是一个悖论。如果这些杂志的主编去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转一转,可能会沮丧地发现,在他们希望拉拢的读者的步行可及的报刊摊上,只零星地挂着几张晚报以及一两份像《特别关注》这样的杂志,而自己在北京某个编辑部里制作的杂志,正是屌丝看不到的杂志。
另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是价值观在媒体中的归属权问题。传统媒体从业者习惯于区分个人作品与职务作品,但这样的区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新闻中体现的价值观最终该不该是一个集体意识的产品?
我们用《纽约客》执行总编辑多萝西·威肯登的话,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解答。多萝西曾在访谈中对比自家杂志和《新闻周刊》的区别:
“我认为比起《新闻周刊》,《纽约客》作者个人的声音更突出。对《新闻周刊》的调查性报道而言,部分是受时间限制,记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深入报道。同时,他们也不允许记者表露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你和新闻周刊的编辑聊过,你会知道他们有一个模式化的工作流程。在过去,新闻周刊在各地的办事处都有记者,他们会在截稿前把采访获得的素材传给在纽约总部的某位作者,然后那个作者会在不同的层面提取所需的素材,着手写作。但这几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在如今的新闻杂志界,有更多的记者自己直接写稿子(而非整理采访获得的素材),然后提交给总部,但这些稿件会被格式化、标准化。新闻杂志上的报道的格式是非常固定的,比如文章的长度。往往时间有限,特别是事件在周三突发,而在周六杂志得出版,就非常赶时间,你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自由发挥了。
“但是在《纽约客》,我们鼓励作者自由发挥,在‘人物特写’这个栏目里你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作者的声音和被访者的个性常常互相碰撞,相映成趣——通常是以好玩并且互动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工作很有意思。这种自由给杂志带来了活力,我想和其他杂志相比,《纽约客》的作者有更多的自由。”
试图用单一要素阐释世界,世界将和瞎子眼中的万花筒一样单调。《新闻周刊》的集体化生产不值得过分指摘,但多萝西起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考路径:在资讯看上去已经过度臃肿的时代,流水线上的新闻是否值得效法。
所谓流水线上的新闻,并不仅仅指日报上僵硬的文字框,它甚至也广泛存在于提供高品质阅读的杂志以及这个国家最大多数媒体从业者的头脑中。今天不少的编辑部都遵行着“可控”思维,比如以公司化运作保证机构运转、实现固定版面预设基调、以想象的读者趣味替代文本个性……最终,我们生产出了具有最大公约数的产品,文本通俗、价值观暧昧。这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说的,把二百二十三张人脸摆在一起,会发现不过是同一张脸的变化,个体将不复存在。矢志于面向大众的杂志,也将面临这样的窘境。灌注集体意识的“可控”的流水线,最终生发出来的却是“不可期待”的情绪。
媒介如何独占?
但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家以往风评还不错且有着价值倾向的杂志或报纸,忽然被人发现濒临倒闭。这是为什么?传统媒体要死了么?我们来看一则“尸检报告”。
1981年8月7日,《华盛顿明星报》在头版刊出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大家都失去了一个坚强、可靠的朋友。”总统信上方的报头,以白宫为背景、用特大号黑体字印着“FINALEDITON”——这是这份华盛顿第二大报纸出版的最后一期,该报编辑在最后的社论中,引用了《纽约时报》同行的话,责怪“华盛顿市民没有用广告和订阅来支撑《明星报》”。一番自怨自艾的无用牢骚后,这份有着将近130年历史、发行量达三十万份的下午报宣布停刊,华盛顿只剩下了《华盛顿邮报》一家报纸。
和华盛顿情形差不多,“黑死病”在八十年代的美国报界传播扩散,很快多数美国城市中,只剩下一家报纸。报馆里净是几十年的老报人的哀叹:电子屏幕摧毁了爵士乐时代以来的美好传统,末日不远了。
把责任推到电子屏幕的头上,这跟我们如今媒体人的思路一模一样。1980年代的晚间电视新闻,让本来规模就比晨报为小的午报和晚报失去了竞争优势;汽车时代与郊区化的过程,更是让以往的社区解体,直接导致报纸订户减少;印刷设备的陈旧以及高昂的更新换代和印刷成本,更令报纸经营雪上加霜。但用这些来解释报纸的困境,足够了么?
别忘了,《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报纸并没有像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被荧幕上的脱口秀名嘴取代,反倒是把《明星报》失落的订户拉了过来,在《明星报》停刊两年后,《邮报》的广告率提升了58%。为什么《明星报》倒闭了,《邮报》却能够继续挺立?我们尝试用另一种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回到1970年的华盛顿,当年若要登一份报纸广告,刊在《新闻晚报》上要花9676美元,刊在《明星报》的前身《明星晚报》上要花12634元,刊在《邮报》上要花16676元。看上去《新闻晚报》最便宜,《邮报》最贵,但精明的广告商却更喜欢后者。这是因为《新闻晚报》的到达率只有20万个家庭,《邮报》的到达率则有50万个家庭,折算成平均到达每个家庭的广告花费,《新闻晚报》要4.84美分,《邮报》则只要3.34美分,投资《邮报》无论如何更为划算。于是,投给《邮报》的广告越来越多,《邮报》得以雇佣更多的人员、提升内容品质与影响力、增加发行量。与此同时,《新闻晚报》和《明星晚报》则每况愈下,1972年和1981年,两份刊物相继停刊。
一旦领先就难以被超越,这种赢家通吃的局面被称为“媒介独占”,它可以从市场的角度解释:当变化发生之际,为什么有的媒体屹立不倒,有的媒体则弱不禁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独占”甚至已经打破了城市与国界间的界限。然而,最令我好奇的是,媒体的“先发优势”建立前,它所获得的初始推力是什么?
影响因素有很多,除了耸动的内容、合理的经营以及阅读群体的成熟等等,有一份研究特别引人注目。1975年,马克尔基金会(MarkleFoundation)资助了一个关于报纸成败的研究,研究人员选择了1960年的164家报纸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失败的报纸比成功的报纸少23%的重大新闻和各类新闻,成功的报纸多21%的地方性新闻、18%的全国性新闻。简而言之,成功报纸的内容品质是失败报纸内容品质的两倍。
说回《明星报》。它拥有里根总统的惋惜和同行的哀悼,看上去价值观和风评俱佳,但是在品质上,它并不如《邮报》高,这让他在变化来临之时,很快成为了牺牲品。前面讲述的《纽约客》的例子恰好与之相反,对品质的一贯追求,令《纽约客》如今的媒体存在分毫不减。
大陆媒体的黄金年代
这些陈旧案例,放到今天,也许依旧可以令媒体人受到启发。与其在新的传播形态的冲击下,每天诚惶诚恐、妄自菲薄,倒不如把身边的编辑记者抓过来,聊聊选题与时事八卦。这好像没有谈论新媒体那样时髦,但足够靠谱。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靠谱媒体在迫不及待地否定自我。
否定与追忆甚至发生在同一时刻。成长于过去十年、年龄在30到35岁的记者与编辑逐渐接管下这个国家媒体的管理权,在这个青涩的换代仪式中,新上任的管理者一方面要对资本市场作出抉择,一方面也乐衷于将既往时光涂抹上金色记忆,并宣称自己是“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批见证人。
在社会学或人类学意义上,这更像是一个重塑“集体记忆”以及“秩序重建”的过程。就像毛时代后,人们面临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以及价值观的重新选择,公社时期的村干部被乡村“能人”们迅速取代,同时关于毛时代的记忆也被重新塑造,被注入了新的解释意义,并被新的参照系所左右。
咸与维新的结果是,直至今天我们还活在毛时代话语的余荫下。媒体的情况多少与此类似,所不同的是,从80年代报告文学开始,大陆媒体继承了毛时代的革命话语,接续了失落多年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并受到80年代舶来的自由主义影响,形成了一套激进的话语系统。称颂进步主义、对改革与保守具有鲜明褒贬立场、排斥精英文化、呼唤大政府介入,对既有权威带有天然敌意、使用宣言书式的书面语言是这套话语系统明显的标志。
对于现代中国的宣示意义,这套话语功不可没。但对媒体而言,这套话语在过去三十年中,已逐渐从腰带变成了束带。媒体发展至今,尽管商业化不断渗入,但话语系统的单调,令主流媒体样式跟上世纪初刊登裸体美人的《良友》画刊以及八十年代露出半个乳房的《大众电影》没有更多区别。我们还是乐衷于展现性与暴力,乐衷于寻找解构性力量,用魔岩三杰的情怀,用“李素丽你漂亮吗”的腔调,做调查和写报道,但在建构性上,媒体的贡献始终乏善可陈。比如,大多数媒体还没学会如何引导议程,反把引导情绪当作了引导议程。
到今天,可供大陆媒体人重复叙述的神话依旧少的可怜,新闻学院的教授将张季鸾时期的《大公报》树立成标杆,努力从其中拣选出新闻理想的影光。但这份“以开风气启民智为主义”为编辑宗旨的报纸,对于今天的媒体建构来说,可资参考的地方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但我们总是需要这样的神话叙事。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不同,他们可以在布拉格之春时,用披头士乐队作为背景音,但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一面要完成现代化,一面还要完成民族的文化叙事。贩卖价值观的媒体,难以逃避这样的使命。如今的媒体人把过去十年形容为黄金十年,也是基于此理,与之前漫长的沉默年代相比,过去十年确实看上去像一个奇迹。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新闻总是被视作同政治社会紧密相关的产物,被赋予一种理想主义色彩。
与“反智主义”为友
大陆目前的新闻理想主义诞生于既往观念崩解的空白时期,所以它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强调独立的智力生活的精英文化消隐,让它不得不选择与反智主义做朋友。
反智主义原本的意义是从常识出发践行集体智慧。1963年,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出版了获得次年普利策奖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书中,他针对60年代,本土主义对全球化文化趋势和都市知识分子的抵抗,以及因教育普及导致的知识民主化浪潮,首次把反智主义定义成了负面词汇。在他看来,反智主义来自宗教传统对科学精神的敌视以及庞大的官僚机构造成的专家崇拜,反智主义者强调物质与实用主义,崇拜常识却难以接受日常生活之外的观念。马萨诸塞州大学的学者艾伦·莱克莱德(AaronLecklider)在今年出版的著作《虚拟蛋头》中继续完善了霍夫斯塔特的观点。莱克莱德认为,二战后媒体对“曼哈顿计划”的报道以及对橡树岭国家试验室秘密社区的揭密,令公众与知识分子间逐渐产生隔膜,知识分子转向政治,这令公众对这一群体的不信任越发严重。
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反智主义思潮普及的成本,同时加剧了其速度和烈度。在大陆,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专业知识分子在媒体与官方的双重漠视下,存在感越来越淡,被推上演讲台的往往是敢于对一切公共事务发表看法的意见分子。尽管对于媒体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与《纽约客》这样的媒体不同,大陆的媒体更热衷于传递加工轻便、抖机灵的知识型产品,而对于提供智识见解,缺乏广泛兴趣。
这种向反智社会主动缴枪的情况,令传统媒体丧失了一贯擅长的思维方式,竞争力也大打折扣,与网络即时消费的轻捷阅读产品相比,传统媒体始终像个“不自信的胖子”。自我戕贼的结果是,它把每一口气喘吁吁都归咎到新媒体的到来,却想不起来过去十年城市机动车的普及以及社区的解体,对用户群体造成的影响,可能远比互联网来得猛烈。
传统媒体面前有许多挑战,但起码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陆的传统媒体并不会倒在互联网所影响的反智枪口下。相反,在社会转型期远未结束时,大陆依旧需要媒体提供的智识。莱克莱德曾总结“脑力”(brainpower)对美国社会转型期的作用。所谓“脑力”,即媒体、作家、艺术家向民众推销智力的方式,通过低成本的流行文化传播,将智力能力传递给以往被视作反智主义者的中下层民众。虽然知识分子价值被削弱了,但“脑力”成为了现代美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工具。
永远不要轻言一个孩子的死亡。传统媒体之于大陆,还处在一个初蒙阶段,反智社会并不会令传统媒体消亡,反倒提供不少可待开垦的荒原。当然,早夭的可能也不容忽视,营养不良随时缠绕着这个孩子。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中,大陆没有一家媒体为行业贡献了具有独特气质、可供效法的方法论,特稿或非虚构写作在语言范式的改善上值得注意,但就方法与思考本身,始终欠缺力道。新闻学、法学、文学毕业生为这个行业提供了最多的智力见识,但这还远远不够,学力不足以及交叉学科的进入匮乏,令大多数媒体的报道还停滞在对新闻与事件的精密加工上,缺少从现象学或观念史角度对新闻与事件的拆解。无法去新闻化的结果是,报道廉价,并且在被印刷成铅字之前就可能已经过期了。追求更长久的产品保质期,这无论如何将是传统媒体未来要思考的问题。
至于现下被讨论得火热的新媒体,或许不用太过在意或焦虑。印刷机统治世界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互联网,变更得是传播手段和接收方式,这是新媒介的变化,无法断言新媒体的诞生。作为一个概念诞生的“新媒体”,在大陆更像是一个被吹得越来越鼓的泡泡,吸引的从业者和投入越来越多,但几乎没有新媒体不是短期逐利的,泥沙俱下之后,至今似乎也没有哪怕一件新媒体产品达到了既往十年传统媒体的优秀标准。
对于媒体形态是否新颖,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通过对英国大众报刊发展的分析,给出了三个评判标准:
1、经济基础:能否跟工业时代有区别。
2、技术水平:无论是纸质印刷还是线上网页,传播的达到率如何。
3、政治环境:即使娱乐小报依旧受制于政治环境,一个成功媒体意味着它能给出时代需要的政治立场。
从资本结构、传播技术以及市场细分当中寻找变革的因子,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死亡。如果不把传统媒体的存在局限在纸质印刷本身,那么作为一种从柏拉图到默多克以来的智识生产方式,在足够长久的未来,它都可以令人期待。